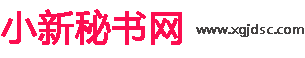散文:父母亲情
我三十七岁那年,母亲撒手人寰;四十七那年,父亲离我而去。那时那刻,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,痛失亲人的哀悲。最近几年,在平时生活的日子里,偶尔碰到同学、同事或朋友家里有老人健在时,很是羡煞;常说“家有一老是个宝”,进门能喊一声“爹”或“娘”,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。羡慕别人的同时,不免回忆起自己的爹娘,早就想写一写有关父母的亲情,可总是拿起笔放下,放下又拿起,因为很多事情已经久远,只能努力地从脑海里挖掘出点点滴滴以作回忆。
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腊月十八,严格说已经到了阳历三六年。父亲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年月,饱受了旧社会的酸甜苦辣。记得父亲曾经说过,九岁那年,日本鬼子到村里抓劳工,大人们害怕都躲了起来,“村长”就派他到鬼子炮楼锄了一天杂草。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后,十周岁的父亲便进了学堂,奶奶一直把他供到西竖中心校读完高小。在那个年代,农家子弟识文断字的寥寥无几,不能不佩服奶奶还是有点眼光的。
父亲的青年时代赶上了社会主义初级社、高级社,跟随着入食堂、大炼钢铁、三年自然灾害、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步入中年,中老年迎来了改革开放。可以说,那代人的经历是丰富多彩、曲折离奇的。可能是父亲有高小文化的底子,很快就入党提拔到大队担任会计,一直干到九十年代初才卸任。五六十年代有点文化的都千方百计到公家捞个“铁饭碗”,国家也急需这样的“人才”,父亲也曾有过一次机会。那时候农村信用社才刚刚筹建,和他一起上高小的同学(叫王书卿,后来从民政局长位子上退休的,九几年父亲还让我给他捎过红枣)从中介绍和极力推荐,眼看着父亲就要捧上铁饭碗、吃上公家饭了,奶奶说什么也不让去,与父亲上学时恰恰相反,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思想束缚了奶奶的眼光。
父亲成年后与相隔三华里的邻村姑娘结成伉俪,她便是我的母亲。母亲不善言辞,只言片语中,知道了她的不幸身世,我外祖父参加八路军战死沙场后,外祖母便起身改嫁。母亲上边有三个哥哥,外祖母只留下了大儿子和二儿子,却将三儿子送给了一百多华里的获鹿县,母亲遗弃到六十华里外的柏乡县一户人家,后被懂事的两个哥哥领了回来,随继父一家生活,直到嫁给我父亲。在我的印象中,每年大年初二会随父母去外祖母家拜年,外祖母慈眉善目,和蔼可亲,当时将两个儿女送走,可能是因生活所迫,出于无奈吧。
有关父母的亲情,是从我有记忆时开始的,虽然充满断层,却包含着爱与幸福的延续。大姐长我六岁,二姐长我三岁,弟弟小我两岁,大妹小我四岁。在最初的记忆里,大姐背着弟弟,二姐便拉着我的小手,经常在一起玩耍。到大姐十一岁时,我们已经是兄弟姐妹五个的家庭了,那时小妹还没有出生。本该走进学堂的大姐,一直辍学在家照看着几个弟弟妹妹。大姐那代女孩很少有人进入学堂:一是新社会到来才刚刚不久,民间流传千年的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古训,仍根深蒂固,虽然父亲识文断字,恐怕脑海里也有掺杂;二是集体经济靠劳力吃饭,多一份人手就会多一份工分。我琢磨后一个原因可能性大些。
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开始,大姐离开了我们五个经常玩耍的地盘,走进了生产队行列。那时男工工分是十二分,妇女是八分,十二三岁的大姐只能挣到四五分。当时,吃公家饭的一个月才挣二三十元,社员工分更是不值钱,一个工好年头才合一毛五六,懒年头也就是一毛钱左右,大姐一天只能挣到四五分钱。小小肩膀挑起了千斤重担。不过,那时物价也便宜,40斤一袋面粉才合七元二角,一斤面粉合一角八分钱,其它粮食更便宜。大姐上四天工就能挣到一斤面粉的钱,对于九口之家也算是雪中送炭吧。
轮到二姐进学堂时,父母好像改变了主意,坚持让她上学。孩子们都怕进学堂,二姐也不例外,死活就是不肯去。呕了几次气后,父母没有过度强迫便放弃了,二姐高高兴兴又回到了我们玩耍队伍。现在说起来,二姐总是后悔的不得了。随着我们渐渐长大,二姐不再当我们的孩子王,也到了生产队上挣工分。其实,父母心里始终惦记着两个逐渐长大的姐姐的前程;虽然木讷的父母不善言表,却把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。
“文革”开始后,国家废除了高考制度,有门路的适龄青年都是通过招工吃上公家饭的。对于这个浅显易懂的门坎,父亲也十分清楚,便默默地托人打听机会和门路。姐姐有个美好的未来,不但是姐姐的幸福,同样也是家族的荣耀。终于打听到县养老院正在招工,父亲便瞅准这个机会,跑了几趟公社找熟人,给大姐要了一个指标。当十分有了八分的希望,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的时候,不料,指标却被另外一个村的支书挖走了。只能说明村里会计与支书在公社书记眼里不是一个等量级。
那几天,父亲唉声叹气的,饭不进茶不思,但日子总要向前过,也只能默默吞下这个结果。后来,棉麻系统招工时,父亲终于如愿以偿,二姐进了棉麻公司上班,尽管是个临时工的身份。两年后,公司精简人员,留一部分,减一部分,二姐属于后者。既然出去了二姐也不想回村,只好找到当时在二轻经理部当经理的大舅。大舅找了棉麻公司经理,最后还是不行,恐怕是二姐没有文化的缘故吧。此路走不通,大舅就说,那就到二轻系统上班吧,二姐先后在贾村瓷厂、竹壁瓷厂干了几年合同工。
“文革”结束后,恢复了高考制度,不再招工,走上了靠自己本事吃饭的年代。弟弟和小妹高中毕业后回到村里,他们都从事过代课老师的工作,时间都不是很长。仅仅这一点,也是父亲运作的,他就那么点能力,用足了用尽了,难道这点父爱还不够温暖吗。后来弟弟妹妹都长大了,小妹是1976年出生的,那时大姐已经19岁,我也13岁了。母亲是高龄产妇,小妹是在郝庄医院产下的。我和大姐赶着牛车到郝庄接回母亲和小妹,途经官都村西南山洼旧公路,崎岖不平,当时村北新公路还没有修通。
从我八岁开始,小学和初中是在村里就读的,那些年可以说是与父母朝夕相处,受尽恩泽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父亲除了白天上工,晚上还得挑灯整理账目,年终能多加几百个工分,一家九口才不至于饿肚皮。也许是有文化的功底,父亲练就了多面手——砌砖、打坯、做豆腐、漏粉条、修理机器……样样都行。生产队解散以后,他还与别人合伙开了多年“花房”(弹棉花)。父亲晚年患得是“肺纤维化”病,他总说与弹花有关系,当时省二院大夫也没有明示,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归医学界探讨吧。
从我记事起,一直到父亲患病前,无论谁家过红白事,或修房盖屋,父亲总是在管事班子里。主家有多少亲戚朋友,有多少帮工,该置办多少桌酒菜饭食,父亲总是仔细核算,既要满足又不能过剩,事后往往让乡亲们心悦诚服,赞不绝口。他虽不善言语,但秉性刚直,是非分明。由于父亲有一手好毛笔字,每年腊月十五以后,百十户的村庄,几乎都来找他写对联,有的来时拿一张红纸,多数是“空手而来,满载而归”。虽然赔了纸张笔墨,父亲仍旧是笑脸迎笑脸送,也许写对联成就了他的收获感和满足感吧。
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,高考后到市里求学,每逢假期还能帮父母干些农活。参加工作后,回家的次数总是越来越少,尤其是结婚生子后,有时半年也回不去一趟。每次回去,父母脸上会笑成一朵花,母亲不是包饺子,就是做她拿手的腌肉鸡蛋韭菜面,她舍不得吃,把自己碗里的腌肉鸡蛋夹给我们。离别时,母亲总要把我们送到距家1000米远的大马路上,等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后,看到母亲脸上依然露出恋恋不舍的表情。车行良久,我们扭回头张望,母亲仍屹立原地一动不动,直到目光中消失对方的身影。
母亲是六十三岁那年病故的,乡下按虚岁算,其实是六十二周岁,从得病到去世只有半年时间。在这半年时间里,兄弟姐妹六个,尽心服侍眼前,先后去河南、武安、石家庄等地寻名医找良药,然而回天乏术。母亲患得是食道肿瘤,自己也能感觉出吃饭困难,尽管儿女们极力瞒着母亲,但性格要强的母亲,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个“癌”字来。尽管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,仿佛仍旧生活在我们的日子里。写到这里,我不由记起古代桓大司马说过“昔年种柳,依依汉南,今看摇落,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的句子。人的生命如此脆弱,愿母亲的在天之灵保佑她的子孙平安健康。
母亲病逝后,父亲一人生活在老房,守着故土,他说这样心里踏实些。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散居在各地,只有大姐生活在老家,与父亲近在咫尺,朝夕相处,每年腊月十八是父亲的生日,兄弟姐妹才会来个大团聚。父亲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,总也闲不住,直到生病前仍然辛勤劳作着。父亲终究没有战胜病魔,于2010年秋冬之交离开了人世。最近几年我和爱人在海南暖冬,爱人曾对我说过,假如当时父亲能在海南疗养,湿润的空气和高含量的负氧离子,滋润着肺部器官,可能会减缓纤维化进程,恐怕会延长几年寿命吧。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养生理念和养生条件,只能是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
常言道: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虽然我们陪伴父母的时间有限,但我们兄弟姐妹继承了父母的正直、勤劳和善良,也一定会将这种基因潜移默化给后代。在写这篇文章时,我好像又看到了父亲的音容笑貌,又闻到了母亲亲手做的腌肉鸡蛋韭菜面的味道……